Address
304 North Cardinal St.
Dorchester Center, MA 02124
Work Hours
Monday to Friday: 7AM - 7PM
Weekend: 10AM - 5PM
Address
304 North Cardinal St.
Dorchester Center, MA 02124
Work Hours
Monday to Friday: 7AM - 7PM
Weekend: 10AM - 5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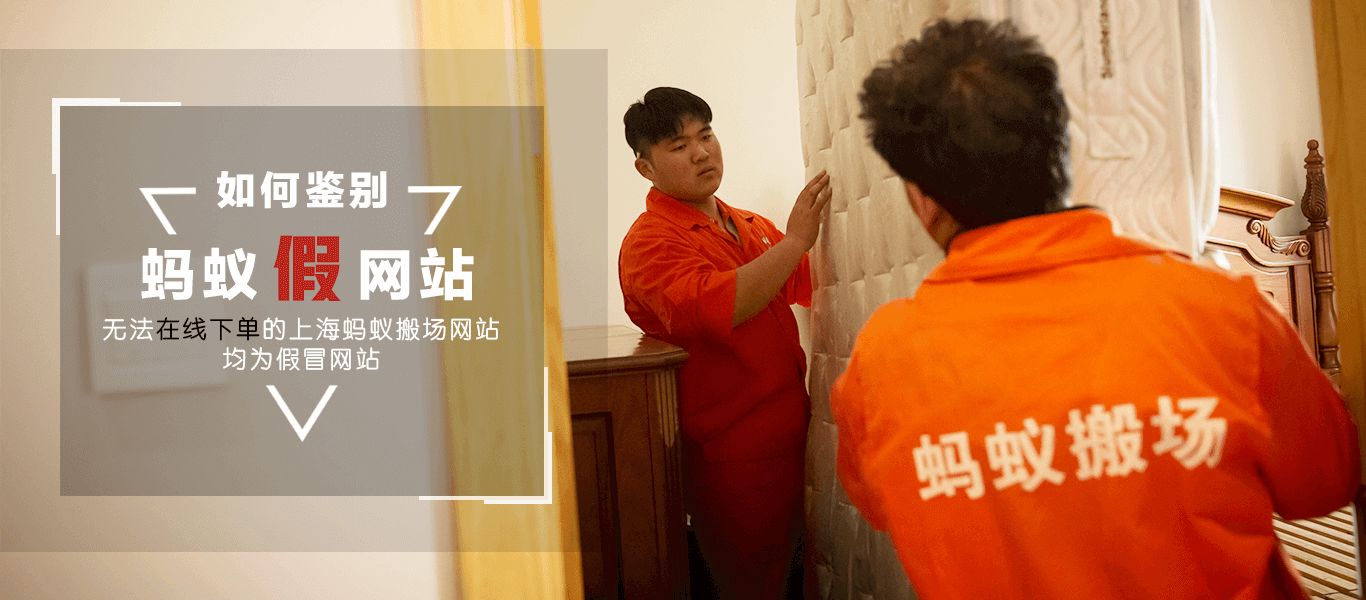
搬家行业门槛低,所以从事搬家服务的人员和企业非常的多,搬家收费也是五花八门,导致整个行业非常混乱,上海其实有22家正规搬家公司,收费标准是由上海运管部门和上海搬场行业协会制定的,找到这些搬家公司基本没什么大问题,服务和收费都是统一的,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解决,但是上海除了这22家以外还有上千家从事搬家的企业和个人,这些公司大多是在互联网上冒充知名搬家公司做推广,低价引流,上门服务时胡乱加价,上当受骗的客户非常的多,这些企业因为是冒牌的,所以留的信息都是假的,出现问题客户投诉无门!上海正规搬家公司搬一户人家收费正常1500元左右,客户找到冒牌大兴搬家公司往往要付出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搬家费用,搬家过程也是苦不堪言!
上海搬家记住重要一点,人工费按时间收取的都不是正规搬家公司,正规搬家公司收费1车1500元左右,收费详情咨询上海蚂蚁搬场公司4008201116;
许有为教授主编
徐有为选编:上海三线口述历史选编(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国际冷战史第十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House,2011 年 12 月上海市正规搬厂多少钱一个月,第 253-282 页。
采访者:许有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编写与研究”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民党特务史、民国土匪史和小三线建设。
上海小三线是上海市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皖南山区着手建设的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中央采取的重大反制措施之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96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开始建设皖南第三后方。 1984年,决定将第三战线无偿移交给安徽省。 经过上海24年的建设,小三线已在皖南徽州、安庆、宣城三个特区和浙江临安等13个县(市)建成81个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 上海共为该基地投资6.4亿元。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5.7万余人,职工家属1.6万余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1500余人。
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为教授受上海近代上海研究中心委托,对“上海小三线建设”进行口述史料采访和收集。 此次发表的四篇口述历史文章是本次活动成果的一部分。 在面试选拔过程中,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婷、吴静,吴晓敏、顾亚军、陆浩轩提供了帮助。 本研究还得到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五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J50106)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 非常感谢。
专访王玉钊
受访者:原安徽省省长王玉钊。
采访人:许有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
组织者:徐有为、吴晓敏
采访时间:2011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北京王玉钊家中
徐有为:皖南小三线调整回上海时,您是安徽省省长。 请介绍一下小三线的背景。
王玉钊:大背景是苏联和我国国际关系紧张,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 在此背景下,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第三战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为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 . 现在工厂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 厂房一分为二,是时候搬到大陆了。 不仅工业交通要搬,学校、科研院所、设计院也要搬。 成昆、川贵、滇赣铁路已尽快修好,做好战备准备。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会议决定,三线建设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保障。 新项目的建设必须放在三线,勘察设计必须现在进行,不要浪费时间。 前线能动,项目就得动。 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由以农业为中心、以改善人民生活为重点,转向加强国防实力、加强第三战线建设、备战备战。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说,不仅中央这样做,各省市也有自己的二线、三线。
徐有为:安徽有没有小三线建设?
王玉钊:对。 1965年4月30日,安徽省委决定成立安徽三线建设指挥部,即安徽小三线指挥部,又称后方建设指挥部。 当年安徽开工的小三线项目有16个。 1970年11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又下达了《1971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小三线。
徐有为:上海皖南小三线有什么印象?
王玉钊:上海的这些工厂,是按照毛主席关于建设三线的指示,陆续来到皖南的。 这些工厂大多设在交通不便的山区。 生活条件很差,困难重重。 特别是文革后,许多工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处于停产状态。 他们都要求搬回上海。 上海也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
徐有为:从安徽来看,情况如何?
王玉钊:根据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1949-1999)》,为确保沪、沪小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为保证一定的独立性,安徽成立了皖南根据地部后方建设司令部。 1976年3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同意上海皖南根据地在屯溪设立中级法院,代行地市司法权。 业务受上海、安徽高院双重领导,行政隶属于上海大后方。 局党委的领导、干警配备、物资装备等均由基地党委负责。 1979年3月12日,安徽省委批准撤销皖南基地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保卫处。
许有为:请您谈谈上海小三线移交给安徽的情况。
王玉钊:1985年1月,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率团访问安徽。 汪道涵,安徽滁州嘉善(今明光市)人。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受到安徽省的热情接待。 经讨论,1月2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沪皖省加强经济合作技术会谈》。 上海“小三线”皖南调整交接协议》。
徐有为:会议纪要的内容是什么?
王玉钊:“沪皖加强经济合作技术会谈”达成意向协议:上海有意与安徽合作开发煤炭资源; 上海将出资与安徽共建铜陵伞形水泥厂,建成后供应上海部分水泥熟料; 按照国家计委、上海市、安徽省、化工部批准的“三、一、一”比例分成原则,追加投资新桥硫铁矿西翼项目; 酒店、改善交通条件、开发旅游产品等; 双方认为,应多层次、多渠道、形式多样,进一步加强纺织、轻工、机械等领域合作; 沪南皖南“小三线”企业及配套,两省市将按照国务院“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原则,进行专项协商并达成一致。
徐有为:那么《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王玉钊:1月28日,安徽省政府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上海市“小三线”皖南地区调整交接协议》,简称《协议》。 《协议》确定,上海市将皖南“小三线”80家企事业单位资产无偿划转安徽。
徐有为:你有多少资产?
王玉钊:安徽固定资产净值3.7亿元,流动资金7887万元。 愿意回沪的员工可以回沪,不想回沪的可以留下。 愿意留在安徽的员工有1469人。 按照安徽省政府就地改造利用的原则,上海皖南小三线工厂全部由军工就地改制为民企。
徐有为:国务院什么时候批准的? 它是如何工作的?
王玉钊:4月17日,国务院批复批准,沪南小三线80家企事业单位工厂由上海转移至安徽。 当时,安徽成立了工作组,由省经委副主任陆廷智负责到各厂办理手续。 当时安徽省规定,这些工厂由当地政府接管,就地由军工转民。
徐有为:军人都转民了吗?
王玉钊:是的,应该说皖南、上海的小三线企业,大部分改制民品化之后,为安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徐有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超过〗
专访朱国勇
受访者:朱国勇,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曾任上海无线电一号党办、厂办书记。在上海三线工作期间,任“305”雷达试验组长上海井冈山机械厂生产组,后方基地管理局科技处干部,后方基地管理局办公厅副主任,调整办公室副主任。
采访者:徐有为、吴京
组织者:徐有为、李婷
采访时间:2011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朱国勇家
徐有为:你上三线之前在上海的学习和工作怎么样?
朱国勇:我1958年在上武八厂工作。1960年6月,上海科技大学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开办工人班,招收在一线表现突出的先进工人生产岗位学习科学技术。 当时,我是区先进生产者,1958年上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青年职工代表大会列席代表。 因此,组织选择了我上大学。 1960年9月,在党的希望和班级的嘱托下,我有幸以工人大学生的身份步入大学的殿堂,接受科技教育。
1965年下半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 1967年11月前后,市革委有关领导要求我校转校生尽快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就这样,我们的转学生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工厂。 向局里报到,选择了去上乌尔厂。
1968年,中央召开“八月十五”会议。 本着“备战、备荒、为民”的精神,决定在上海试制“305”产品,由尚武二厂承担了此次试制任务。 为加快该产品的试制,上海科技大学和南京炮兵学院也派教师参与了该产品的试制。 当时,我是产品试制组组长。 经过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和反复试验,于1970年完成了样机产品,同时在上海小三线继续试制,准备指定生产装备部队。评价。 1971年12月26日,我带着该产品到上武二厂承包建厂——井冈山机器厂。 当时交通不便,没有直达安徽景德县的汽车。 为此,我们乘火车经南京,次日抵达芜湖,再乘长途汽车前往景德县城。 从县城到井冈山厂区有30多公里的山路,没有班车到厂区。 为此,四工区(后方基地管理局一电公司前身)的同志打来电话,厂里派车来接我。 我们被一辆大卡车接走了。 因为是山泥路,车子经过时会扬起灰尘,就像漫山遍野的浓雾。 在基层三线工作近19年,1988年4月回到上海。
许有为:作为三线小前线的老同志,请介绍一下三线小前线的概况。
朱国勇:上海小三方面军的建设始于1965年,当时叫“229”司令部,后来更名为“812”司令部。 与“507”司令部合并后,1973年4月改称上海大后方基地管理局,企事业单位81家,分布在皖南山区12个县和浙江省临安县。
上海市小三线建设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小三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上海市有关工业局根据小三线总体规划负责对口承包建设。三线建设和产品配套的需要,包括选址、基础建设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配置,可以说是当时的骨干队伍,即“好人好马好刀”和枪”。 小三线建设初期,采取了边生产边建设的政策。 在安徽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拼搏,到70年代初,生产规模已初具规模。 后来,通过逐年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企业管理不断改进,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企业生产已达到设计方案的要求,形成了正常的规模生产。
徐有为:你对小三线的初步印象是什么?
朱国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些单位大多位于远离城镇的山沟里。 当时是出于备战的考虑。 虽然隐蔽,但如果山上被大雪挡住,会给工人的生活和生产运输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们曾数次遇到大雪封山。 很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都要从上海等地运进来。 虽然汽车可以加装防滑链,但难度还是有的。 上海小三线工人的生活非常艰难。 住的是干房子,文娱生活很无聊(那时候还没有电视)。 公司放映组每月轮流到厂放映电影1-2次,单位每周为员工家属送蔬菜1-2次。 稀有的。 员工基本多年不回上海,只能在春节期间回上海与家人团聚。 即便如此,小三线工人还是安心工作,很少抱怨。
徐有为:那你具体的工作情况呢?
朱国勇:我先去了井冈山机械厂,主要是继续试制“305”产品。 在井冈山机器厂工作两年多后,1973年6月调入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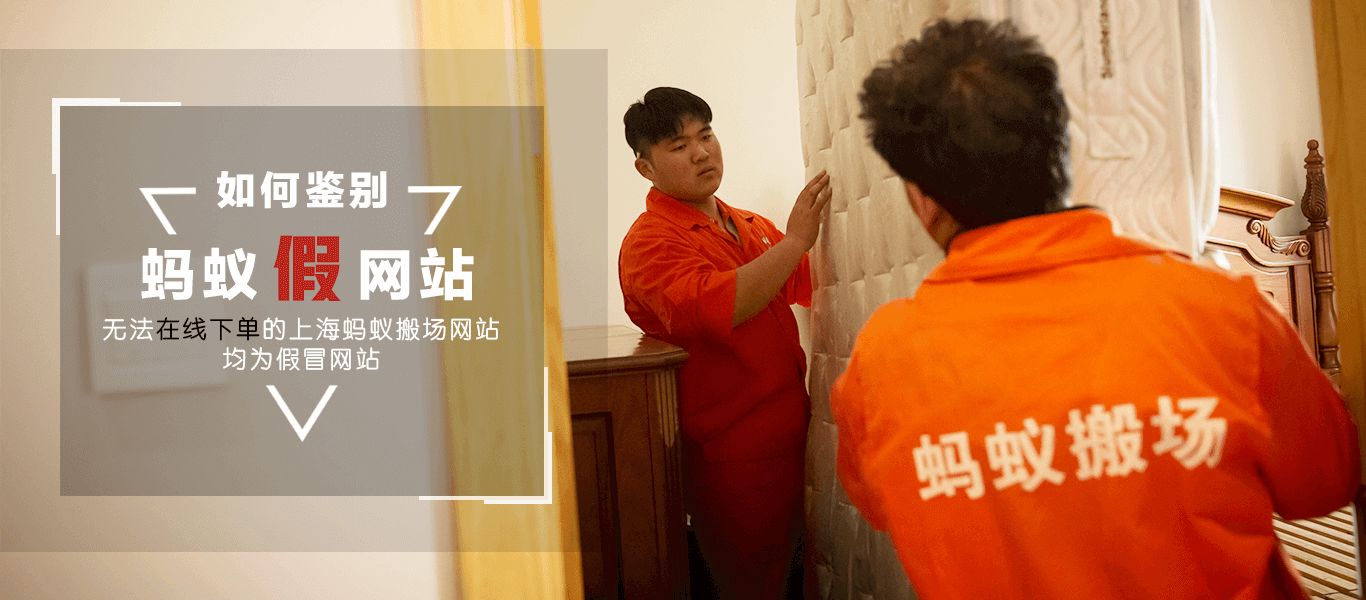
吴京:请介绍一下后方管理基地局的内部机构。
朱国勇:文革时期,后方基地管理局的管理机构,业务部当时叫生产大队上海搬家公司要多少价格才能搬,大队、大队都是大队。 还有一个政治部。 粉碎“四人帮”后,成立维新部。 1984年,为适应小三线调整的需要,将原基建、物资、劳资、金融、科技、生产、物流。 后勤负责所有票务、医院和食堂。 文革时期的生产队也是这样,包括这些业务部门。 我去的时候在制作组。 后方是一个小社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管理。 除生产企业外,还有交通运输、中小学、医院、防疫站、“五七”干部学校等单位。
吴静:局科技处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朱国勇:主要是抓好产品质量、信息新技术推广应用等相关工作。 军用生产不同于民用生产。 质量不仅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更关系到士兵的生命安全。 因此,必须严格控制质量。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军方代表将领证,产品不予受理,产品不予发货。 所以一定要把质量关好,质量是重中之重。 为此,各厂的理化分析室首先要检查原材料的质量。 工厂建立了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 辽源机械厂、光明机械厂QC小组在兵器工业部全面质量管理大会上公布了成果。 后方基地管理局理化分析协作组在兵工部青岛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后方工厂的军品生产,都是配套的。 如果一个工厂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其他工厂的生产进度,所以需要协调同步。
此外,由于小三线企业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工程技术人员很少外出学习交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难度加大。 1978年8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金属切削交流队和普陀区金属切削交流队请来了朱衡、盛力、唐英斌等全国劳动模范交流组到三线传授经验,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吴京:上海的三线学校有没有科技成果?
朱国勇:上海共有81家皖南小三线企事业单位,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建成的。 20年来,小三线员工辛勤耕耘,辛勤耕耘,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军民产品。 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山区开发做出了积极贡献。 例如,5339厂研制的DG-1多功能电子计时码表就是一款性能可靠、计算标准、抗干扰性强、体积小、重量轻、应用广泛的产品。 在我国首次运载火箭发射试验中圆满完成。 完成任务,获得国防工委嘉奖。 又如光明机械厂与同济大学合作,首次应用气浮法处理电泳漆废水获得成功。 经有关单位评价,认为该新工艺为我国电泳漆废水处理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跃进机械厂热处理新工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其他单位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
吴京:三线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如何?
朱国勇:小三线开始投资基建,但还没有形成正常生产,当然是亏损的。 随着生产线的建成,由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大部分企业开始逐年盈利。 到1988年小三线调整结束,总体上没有亏损。
徐有为:小三线后期军转民的情况如何?
朱国勇:在小三线企业军转民转的初期,企业比较困难。 一是原材料要从上海运进来,产品要运出去,成本比较高。 二是产品销售难。 当然,在上海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下,一些工厂增加了一些民用产品的生产,如井冈山厂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光明机械厂生产的电风扇等。 也有不少工厂原本生产军民两用产品,在转民产品方面具有雄厚的基础。
吴京:和安徽当地人的关系怎么样?
朱国勇:上海的小三线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山区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比如小三线建成后,山通了路,农家也通了电,可以经常去小三线看电影。 这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好处。 此外,小三企业也在一些物质方面给予了地方政府积极的支持。 总的来说,两地关系虽然出现了一些矛盾,但后来都处理得比较好。
徐有为:小三线后期遇到了哪些困难? 如何看待小三线的调整?
朱国勇:上海建筑皖南小三线企业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 20多年来,通过广大小三线职工的艰苦奋斗,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企业从最初的亏损到逐年支付利润。 但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市正规搬厂多少钱一个月,也存在人员变动、信息不畅、军品任务不足、民品生产成本高、销售难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1984年,根据国务院领导关于振兴小三线的指导精神和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整、转型、发挥作用”的方针,上海市委、市委政府决定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调整小三线。 . 1985年1月,上海市副市长朱宗保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同志。 与安徽省副省长邵明及省有关部门同志在合肥就上海市小三线调整进行了充分交流,达成共识。 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小三线的调整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发展横向联动,人尽其才,人尽其才,人尽其才,产能得到充分利用。 上海方面表示,愿意在调整后无偿将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转移至安徽。 国务院(85)国办函批复上海小三线皖南地区调整移交协议。
上海小三线的调整交接工作是一项繁杂而细致的工作。 一方面要抓好调整和生产。 要按政策做好返沪返湾人员安置工作,稳妥处置。 两地关系不错。 小三线调整交接的关键是人员安置,因为钱和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是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 为此,我们做了很多详细的调查和调查工作。 在两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根据企事业单位具体情况,分批、分阶段进行交接。 在交接过程中,沪皖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顾全大局、了解大局、统一认识、相互协商。 历经5年左右,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工作基本完成。 至此,小三线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和评价上海小三线的优缺点。 我觉得应该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出发,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和评价。
徐有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超过】
陆建昌专访
受访者:原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后方瑞金医院政工科科员,现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采访人:吴京、陆昊轩
采访时间:2010年3月29日
面试地点:上海大学艺术学院A座618室。
1、上安徽小学前培训
我们当时不知道第三行是什么。 1970年以前,67、68、69班的学生都是“全红”,全部上山下乡。 据说周恩来后来说读书要连续,不能间断。 大学不成立,国内就会出现知识鸿沟。 于是在1970年上海搬家公司什么价格表,原定的中学生全部务农的政策被放宽了。 大学一方面开始招收工农兵,另一方面允许设立中等技术学校,如技校、医学院等。 When this method was implemented, it happened to be our turn to graduate. When I was assigned, I could go to farms in the suburbs according to my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policy of "one worker, one farmer", that is, one "hard market worker" and one "worker". foreign farmers". One of my family has jumped in the queue and settled down outside, and the other is working in Shanghai, so I have the conditions to go to a farm owned by the city, or to work as a "foreign worker" (that is, to work in an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 in another place). If there is no "one farmer" in the family, it must have gone to a rural area or a farm in another place, or jumped in the line to settle down. Many people in our class just went to other places to jump in the queue and settle down. For conditions like mine, there is another assignment called "no-destination training", which only began to appear in 1972. Those students who are designated as "no destination training" have not decided where to go after graduating from middle school, but they must be assigned to other places, but they are first arranged in a certain unit in Shanghai (such as factories, enterprises or hotels) Classes, etc.) to be apprentices, for training, and after two years, they will be assigned to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or other units in other place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graduates from the "no destination training" were assigned to Meishan-Nanjing Meishan Project, and some were assigned to Tongling, Anhui Province or other places farther away. Our hospital also had some "no destination training" graduates who were assigned. They are arranged in the logistics department, such as technical team, fleet, canteen, etc. Most of them are asked to do corresponding work based on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learned during the training in Shanghai.
I was good at studying in middle school, and the head teacher wanted me to continue studying.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wo ways to continue studying, one was a technical school, and the other was a health school. I thought that boys were all going to a technical school, so I guess they would be assigned to the factory to study in a technical school. When the notice came, they went directly to Ruijin Hospital in the rear. Worked and was surprised. When a group of us (all graduated in 1972) reported to the Ruijin Hospital in the rear, the hospital planned to conduct medical training for us. Our boys study medicine in two ways, one is oral medicine and the other is pharmacy; all girls study nursing. We didn't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it was all assigned by the teacher, and I was assigned to learn medicine. At that time, the conditions for pharmacy training at the Ruijin Hospital in the rear were relatively poor. After we arrived there, the hospital sent us to the Shanghai 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 to take a basic course in pharmacy for one year. In the first year, we took classes with students from the 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 of David. At that time, Qian Yi, a teacher from Ruijin Pharmacy Department, and several other teachers from the 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 (some of them were already associate professors) gave us lectures, and the classes were very good. The full name of the Second Medical School is "Shanghai Second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ealth School",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current Xinhua Hospital.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merged with the Jiading District Health School, which was located in Malu Commune. After one year of basic theoretical study, we went back to Ruijin Hospital for an internship. We have learned a lot of chemistry in pharmacy major, especially organic chemistry. When we were studying, we were all determined to make anti-cancer drugs in the future. Later, we went back to the hospital to see how to make anti-cancer drugs under such conditions. Ah, I was discouraged.
2. Specific work in the primary third line
After I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I first worked in the pharmacy department. The pharmacy department has several departments including outpatient pharmacy, ward pharmacy, sterile preparation room and general preparation room (we are used to calling it "pharmaceutical factory"). I have worked in various positions in the pharmacy department, such as dispensing medicines for patients in the outpatient pharmacy, Go to the drug storehouse to purchase goods, reconcile accounts, etc. Some medicines used in the hospital are manufactured by our own pharmaceutical factory and are internal preparations. For example, we can make some ready-made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the beverages we drink now, and some ointments by ourselves. The conditions of the pharmaceutical factory are very good; the pharmacy in the ward is only limited to dispensing medicines for inpatients. Take over, the doctor will make rounds after 8:30, and the nurse will prescribe all the doctor's orders before 10:00, and then send the prescription list to the pharmacy of our ward, and we will dispense the medicine. Glucose saline is often used as a sterile preparation, because the demand for large infusions is hug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transport them from Shanghai, so they must be produced by themselves. Now it's completely corporate in nature, and it can be sold if it's done. But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economic awareness in this area. Everyone lived in a big pot. Your salary is 36 yuan, and I am also 36 yuan. I didn't think of this. There is no such condition.
At the end of 1974, another colleague who worked in the pharmacy department (he was my middle school alumnus and came to Ruijin in the rear with me)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hospital pharmacy department to the hospital polit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Because the hospital needs to develop and lacks personnel, we are transferred here and counted as training objects. The Politics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rganization and Propaganda, just like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urrent Party Committee. However, in addition to cadr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work, the organization team also takes care of the work of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of the unit (labor wages and personnel affairs); the propaganda team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political studies and general propaganda work.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political study tasks were many and heavy. Political study was done twice a week, and there was also "reading every day". Tasks were assigned every day, such as finding articles and writing articles, etc. One is to study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above, and the other is to use your brain to figure out how to organize everyone to study.
The leaders of the Politics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re two veteran cadr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a section chief, a deputy section chief, and 4 others. One of them is a lecturer transferred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He has good eloquence and writing skills. It was he who wrote it, the other was me and 3 other young people.
At that time, in order not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masses, it was stipulated that our cadres should go out to work every Thursday. My work in the hospital, such as planting watermelons, going out to pick herbs, etc., gardening, digging and building fish ponds. There is an old maste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of our pharmacy department. He knows that there are more golden cherry seeds and Capsicum chinensis in Anhui (the syrup of capsicum chinensis can relieve jaundice for jaundice hepatitis), and he can pick them. He compares all the herbs in this place in Anhui. Received, so we will go to pick herbs basically every week. Since the leaders of our political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lso went, the first leader of the institute, Lao Cui, and the second leader, Zhang Guifang, all went together, so the conditions were relatively good. First, we went to the driving class to book a car, and had dinner outside at noon. In summer, we are surrounded by rice fields and villages, and we help the Xionglu brigade in the nearby countryside to harvest.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area is very good. The local area knows that your hospital is a big family, so they are more polite to you. This is a bit like 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 Because basically we give it to him,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us, they create conditions for us, very kind.
According to Chairman Mao's "June 26" instructions, we organize a medical team to go to the nearby villages every year. In fact, it is very simple, that is, the major departments of internal medicine, surgery, gynecology, and pediatrics select some doctors to go to the local towns and villages for medical tours. In fact, this method is not bad. When people see that you are a great doctor in the city, they will let you see many problems, and these medical treatments are actually free. They will give you some medicines without money. The money for the medicine was taken out of the hospital,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hospital's finances were all paid by the state, and whatever was needed was allocated from above. So Ruijin Hospital was in a financial "deficit" at that time, and often needed to collect money, which we jokingly called "debt collection". Every year when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pproaching, our hospital will organize a group of people to go to the nearby villages, the farthest is to Tunxi. Because our hospital also serves local patients, local patients do not need a deposit when they come to see a doctor, and we will see a doctor when they come. If you are hospitalized, there are a lot of expenses in the ward, and if you can't pay the money, you owe it.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you cannot b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if you have not paid all the money, because you will have to go through the discharge procedures at the end (just like our graduates leaving school, you need to be stamped by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you cannot be stamped if you have not paid the fee in full. You can't get out of the hospital gate. But the hospital didn't let them go out, so they ran away secretly. These patients didn't even want the backpacks they brought with them, and just sneaked away. But the patient's name and address are there when registering. We search based on this, and we can usually find them, but the patients can't afford it, and they are very poor.
At that time, in addition to sending logistics staff to collect debts, the hospital would also recruit some medical staff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I also went to collect debts at that time. I was already working in administration and I remember going there with my colleagues who worked in the small shop at the hospital. We went to Shexian County to collect debts from a patient in depth. The traffic in that place is not very convenient. The goods are transported in and out by boats, but the things are very cheap.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described by Tao Yuanming is that place, but of course this is just a legend. Anyway, traffic inconvenience is real. After the patient was hospitalized, although his condition was under control, the patient fled back. After returning, the patient eventually died. He owed a lot of money at that tim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often such situations, so you go to the patient who escaped due to arrears, and ask if so-and-so is there? 他说是的。 Have you ever been hospitalized? he said yes. How much does he owe? He also admitted it, but he still hasn't come out yet. We also went to the commune first, and the people from the commune accompanied us down. This is very formal. We send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e, explaining who to look for and how much money we owe. One year I remember going with a secretary from the commune. We drove to the commune, and then walked to the village together. After finding his home, he was found to be extremely poor. It can be said that there is really no furniture in his house, just a broken bed and a broken stove, and the walls of the house are bare. We stipulated at that time: If you go outside, the subsidy given to you in the hospital is very small. You can go eat that meal of the locals. He couldn't give us anything to eat, so he drank a few mouthfuls of thin porridge and ate some pickles.
He is so poor, we are all embarrassed to drink a few mouthfuls of porridge, so we follow him hungry.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is person, so I told the person next to me, forget it, because I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ble to get it. It's useless to stay with him any longer, and it's useless to sleep with him all night. He was very polite and said that he really didn't pay. We reported all these situations to the hospital after we came back, and the hospital had no choice but to apply to the higher authorities to write off a sum of arrears every year, just like a bank with bad debts. Our hospital has to write off a lot of bad debts every year, which is this kind of arrears. This kind of arrears was still paid by the state, because the hospitals at that time were fully funded by the state.
At that time, we stipulated that it was also open to people from third-tier factories. How did people from third-tier factories come to see a doctor? They all park their cars once a week, because their factory also has its own infirmary, just like the school hospital, where minor ailments can be treated, except for emergencies, when he specially sends a car over. Because there is still a long distance between factories and between units. Two hours is close, and the winding mountain road is easy to drive around. If it is an emergency, seek medical attention immediately. I don't talk about paying first and not paying, because there are no big problems in the factory anyway. They are all labor insurance, and he will not renege on his debts.
Althoug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our rear hospital construction is to serve the third-line factories, we also accept local patients, and some of the local patients often come from the city.我们这个医院在地方上很吃香,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高。当地的县级医院肯定是比不上的,地级市黄山市的医院也不行。所以他们那里的领导都经常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生病了都到我们这里,住在我们病房。安徽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曾在我们医院病房住过,他原来四人帮粉碎前是受打压的,后来四人帮粉碎了,他就解放了。地方上的领导对我们医院的人员很客气,并且大力支持医院的工作,你们需要什么就尽可能提供么。那时我们这边业余生活很单调,怎么办?当地领导说叫文工团来演出一下。当时二炮部队有个文工团驻扎在屯溪市,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演出。还有就是地方上的放映队经常来医院放电影,我记得除了地方部队的放映队之外,当时还有个“三·二一”地质队驻地屯溪,他们有一个放映队,也常来我院放电影。那时后方基地也有个放映队,在三线厂巡回放映,基本上一个月来医院放映一次。
三.小三线时的日常生活
我们这个医院员工几乎全是上海人,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地招工进来的几个人员,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后勤工作。当工务员,分发饭菜,食堂里面做副手,送煤等,因为没有受过训练,不能做技术工作,在医院里也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总体上来讲我们那里也等于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唯一的一个不足就是有了钱没有地方花。他们老医生拿的还是和上海一样的工资。我们拿的是三线的工资。当时工资有地区差别,安徽这个地区属于四类地区,上海属于八类,如果我们完全拿四类,他们也亏待我们了,所以两个折中一下,搞一个六类,六类这个档次的起步工资就是33元。我在那八年,都没有加过,那个时候是不加工资的,文革当中等于没有加过工资。但当时东西便宜,食堂吃饭,一块大肉,一点青菜,一毛五分。
我们在那里吃的挺好的,医院食堂经常开了车子到屯溪去采购的。我们所有吃的用的都是到当地的市镇上去买的,其他小三线工厂也一样。当地的农副产品很多,粮食也很便宜。那里的米都是新米,不像现在。以前我们上海米店里卖的都是陈米,新的米藏起来,陈米拿出来卖。那里都是新米,很好吃。
当然买东西不方便,这和上海是不能比的。上海到处都是店,他们那边的店都是在市镇上的,所以我们买东西必须要放车子开出去。一般走二十分钟到雄鹿一个车站,只有一家很小的店,因为那里店搞得多没有人买的,农村里面消费水平本来就很低,所以开得店不能多,一般在绩溪的比较多,我们过去大概是三刻钟到一个小时。到县城里面还有点东西,但是也不多,和我们上海是没法比的。所以我们经常到歙县,历史上曾是徽州府;还有就是到屯溪,地委一级的,比县还要高一点,那些地方比较多。所以我们食堂后勤部门的每天都放车到那里去买。
我们上海瑞金医院有个支内组,支持内地建设。这个支内组有大概有5、6个人,联系上海瑞金和我们后方医院之间的人员,处理两地的相关事宜。主要是采购药品、采购设备,后方也是一个机构,所有采购的东西都由支内组在上海买了以后运到这里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支内组的人员也在不断变动。比如你在安徽工作有困难,就把你派到上海来,在支内组工作。这样你在上海有人要照顾就好办了,不然一个独生子到那边去,父母亲都在上海,有什么事怎么办?不可能来来去去,若是在支内组工作,每天就可以回来了。另外老医生张贵坊他们69年带队去的时候,他们的户口都是在上海的,人在那里工作。老的员工即从瑞金医院出去的,户口都在上海。我们这些人等于是从学校里直接分配的,这个户口就迁过去了。
我们每年有20天的假期,事业单位都一样,现在也是这样。过年都是到上海过的,在那边过的也有,一般是一家三口都在那边了。回去的话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乘当地的长途车,还有就是单位的班车。我们一般都是乘单位的车,因为是内部的车,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象征性地收点钱。从安徽回到上海,我们当时要做12个小时。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杭州方向走,一条是从湖州另外一个方向走,反正都要经过宁国。宁国要比我们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先到宁国胡乐,那里是古田医院(上海仁济医院支内),我和里面的很多人还是比较熟悉的,我的几个同学也在那里,宁国的小核桃很多,我们很喜欢吃,有时打个电话,让我的几个同学送过来。
说实在的,三线厂里面也有好处,我们在医院里面,能结识很多朋友,当时年纪轻大家都讲义气,过来我会帮你找医生看病,我对他们都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乐意和我交朋友,在后方三线厂我可以一直从这里吃到那里,今天到你这个厂里玩了,明天到另外一个厂玩,一个圈子可以兜下来。
后来还参加过后方的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江曾培,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他当过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和社长,这个人来头蛮大的。这可能也是当时市政府的一个要求,当时要求加强对后方三线建设的文艺宣传等等。他退休后,有时还能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看到他写的短文,经常对时政进行批评,很有水平。
我在后方工作的8年间,基础设施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72年的时候公路都开好了,建设得差不多了,要不然大部队也开不进去,当年张贵坊带领的先头部队去搞筹建的时候,由地方上帮助建造房子,那个房子叫“干打垒”,和我们这里不一样,下面都是用石头砌的,但外表很是不平,结构很差。
我们一开始住的房子是医院的职工宿舍,就像学校的集体宿舍,我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要给他们房子,因为那时候都是由单位分房子的,包括我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学校也是分房子,你如果要成家的话,会分你一套房子。
我们的宿舍区有两块,一块位于“黑风口”,这个地方热天很凉快,所以叫黑风口。另一个地方位于“老虎灶”,从黑风口过去大概五分钟,两个地方各是一排房子。我们去得晚,又是单身,所以都住这里,这房子就在山脚下,隔音效果很差。我们刚去那里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很热闹,楼上住了几位医生,下面小护士声音很吵,他们上面就“噔噔噔”地敲,隔音条件很差。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我们搬到病房楼上的空房间去住,当时医院住房管理上面是很松散的,因为都是医院造的,如果不愿意住原来的房间,只要跟后勤的讲一下,有空的地方就可以住。所以后来三楼病房靠近食堂部分作为单身宿舍,有时候也是作为招待所,我那时候很多同学到黄山去,回来住在我这里。我跟管理招待所的人讲一下就好了,都不要钱的,都是医院的员工,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大家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关系都很好的。
唯一觉得不太好的就是当时比较闭塞,不能回去,不像现在有手机,那时只能打长途、发电报。但是我们医院还可以,搞了一台投影的电视,很大。当时20世纪的70年代,根本没有像现在的电视机,搞了一个大的投影仪一样的电视机,放了以后它投出去后放大,就像小的电影场一样,但是这个电视机质量不过关,一直要请后勤工程师来修,有一个工程师是交大毕业的,因爱人在医院工作而调到一块儿。到我们医院只能修仪器设备什么,有些人本事很大,但只能委屈他在这,经常让他修理设备。
如果在上海,你想干嘛就干嘛,可以逛街等等。在这里,你想看电影,除非我们医院放,不然你得跑到绩溪去看,那得花很多时间,这个划不来。还有买不到书,虽然我们有图书馆,但是大多都是医学书,而且对老专家来说,这些书还不够,是有限的。在那里也不觉得苦,因为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市场这么丰富,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赚大钱,这样的环境下是不会想到的,应该说苦是肯定不苦的。
其它工厂应该也都不会苦,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厂和医院都是独立的单位,出了医院出了厂之后周围都是农田和荒山,没有更加多的社交。我们医院算是信息交流比较多的,所以很多厂的员工都跑到医院里来。医院里护士多,很多厂的小青年不甘心找当地的姑娘,就会跑到医院里来找女朋友。

当时我们感觉当地的人生活还是可以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皖南山区属于安徽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还是大米呢。我们知道80年代要造上海到黄山的铁路,但是当时我们就已经回来了。这条铁路是经过绩溪的,原本只有一条公路,但是公路总是没有铁路好。
四.在瑞金医院的周边生活
后来我们医院开办了一所附属小学。主要是我们医院自己职工家属的孩子在里面读书。那时我已调到政工科做行政工作了,有时也担任那里的小学教师兼些课程。但是因为学生人数不多,读一年级、读两年级没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生源主要是医院职工家属的孩子,地方上招来的职工人员的孩子可能也会过来几个。我们这里小学的老师一般是我们医院的家属。比如张美玲护士长的丈夫是上海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分到四川工作,当时有个规定,支内的家属可以把他的户口迁到我们三线来。张美玲的户口是留在上海,但是因为她是支内了,她的家属可以过来,她丈夫过来以后就来小学教书。后来八几年的时候他回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在那里退休的。八十年代部队开始评军衔,他进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之前工龄较长,进部队后是算军龄的,评军衔一下子就是中校,因为资历老,最后在上校的位置上退的,享受军队的待遇。我刚刚考完大学,他来看我,就说部队一切待遇都很好的。还有一个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讲师,他的妻子是我们化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也调到后方医院来了,他跟我在一个科室工作,七十年代末他到苏州铁道医学院去了,他在那里退的。当时小学里的老师用不着高层次的大学教授去讲,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当他们的老师。还有一个张春宝是海关学院的,现已经退休了。他当时在那里,负责当校长。他是科班出身的,是搞法学方面的,因为他的妻子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内科医生,后来也是上海瑞金医院一位内科主任医生。他调过来以后让他去办小学,当校长。我们医院搬回上海来以后,他就回到海关学院去了,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回归的。
当时有一个人的户口在小三线的话,他的家属也可以迁过去,这是一个特殊的政策。我们还有一批是属于崇明的人,后勤部分都是崇明的人来了很多,他们原来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五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把他们这些临时工都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就答应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国家环境变好了,还是请你们过来。后来搞三线建设的时候就通知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去,不愿意就仍然在崇明工作、务农,如果愿意就到医院里工作,所以他们过来好多人。他们当时都在三线医院的后勤部门。后来三线医院撤回去了,他们有些人都是作为瑞金的员工,在瑞金医院的后勤部门工作的。
当时的矛盾就是思想比较左。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员工收听敌台,当时说美国之音是敌台。这个员工是在电话总机房工作,当时电话转接都是人工的。电话室里面都是轮流值班的,这个小伙子值班的时候跑到医院广播室,他自己在偷听,想不到扩音机与喇叭的线路没有切断,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声音突然从广播里转出去了,我们在路上、操场上的都听到了美国之音。那时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在医院(我们医院是上层建筑嘛,八五钢厂的工人到我们医院来当工宣队),听到了,就上纲上线搞阶级斗争。要他交代写检讨,之后把他调到外面做体力劳动,本来像机要员一样的工作性质,后来做后勤的劳动力,是最低层的。
五.奋战高考,回到上海
“四人帮”粉碎之后,好像有一些消息,我们感觉世界开放了,以前亲戚在海外,是作为一种重点监视的对象,不敢讲出来。78、79年后,有些人家里有海外关系的,亲戚在香港、台湾或者美国,会带来一些外来消息、物品。那时候最时髦的就是带来一个大喇叭一样的录音机,放一些歌曲什么的。那时候我们思想不解放,单位里像邓丽君唱的那样带有爱情的歌曲还是禁止的,后方三线厂的青年人只能在寝室里偷偷的放录音听,很独特,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歌曲不一样的。
当时只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本是想读工农兵大学生的,但是是需要单位领导同意的,领导把我们当接班人培养了,就不放我们,我们单位有了选送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单位里把很一般的青年人送出去读,如一些后勤部门工作的人员,我们真是气死了,但也无可奈何。后来高考开放以后,他们也不同意我们走,我们就跟他们吵,因为领导不同意,单位就不盖章,我们就没办法报名。最终领导还是同意了,后来我就参加高考了。
说到后来回上海,也没想过,直到恢复高考之后,我们才发现要变化了。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在山里有个缺陷就是信息很封闭,包括关于高考的信息。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们都没有准备,书都没有,医院里几十个人去高考,结果可想而知——全军覆没。没有书怎么准备呢?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当地进来的人,他读过高中的,有一套教材,他的这套书就被别人借去,我们轮着看,但是我们当时的理科知识仅仅是初中水平,高中的教材自己看毕竟有很多看不懂。不管怎么样,我从头开始学。我觉得当时一套数理化丛书是很好的书,我们当时都看不大懂,很累。当时我没弄到一套,只弄到几本,我当时解析几何很差的,就向医院里的家属老师请教,这些家属老师由于他们的配偶支内,所以他们调到后方瑞金来工作,虽然不做医生,但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理科功底很好,有他们的帮助,真是我的幸运。另外,我同原来的中学班主任联系,她是华师大毕业的,在上海一所中学教化学、数学,我就向她求救,让她给学生做的卷子寄给我一份,这样虽然不全,但至少我有了一套资料。我还去买一些高考复习资料。(其实这个路子是不对的,因为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学到,而且这些复习资料都是别人考过的,这些题目不会再出现的。)就这样白天上班,晚上准备高考的东西,一直到两三点才休息,第二天照常上班,很累。但是那时候想拼出来就好了!80年我们医院十五个人参加高考,就我一个人考上了。
六.小三线同事的出路与近况
我们没想到都撤回来了,如果说一辈子都待在那边的话,我们会不大甘心,对于那些比较年老的人,他们退休可以回来,但是我们当时去的这些年轻人,考虑到将来的孩子,如果以后在那里读书的话,不太放心的。但我们当时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是属于上海的小三线,这样就对我们有利了。
当时我的户口是迁到安徽的,户口不迁去我可能不会考大学了,我就读在职的了。按照当时的情况不通过高考是迁不回来的,不过现在都迁回来了,因为后来已经彻底连根一起拔回来了。你只要回到上海有什么落实单位的话,只要打个证明,就把你迁回来了。但是安置的时候,都给你分房子,我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们很多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回来都有房子了,他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浦东公利医院那边。
撤回来之前,不通过高考的人是没条件回来的,到了撤了的时候才能回来。我是已经脱离了医疗行业,他们回来了还是在医院里,搞行政、搞业务都有,现在很多护士都退休了,我们中学里去了7个人,当护士的都退休了。没想到医院会撤回来的。本以为一辈子就在山里,做山里人了。想来想去,没有想到这个医院会撤掉,一撤等于原来的东西都废掉了。当时林彪事件发生,中央在“珍宝岛事件”后警觉了,可能要打仗,那时就考虑建立后方,建立大三线还要建立小三线。邱会作(林彪的死党,地位很高的,属于政治部主任之类的),他去安徽视察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好,就定下来作上海的小三线,当时国防工办需要搞小三线。小三线要把一些军工厂迁到那边去,安全起见,要分散,但是你这个厂过去,工人会生病,靠当地的医疗设备肯定跟不上的,要求医院撤一部分过去,所以我们这个都是东方红医院几零几信箱,都是保密的,没有具体地址,每个厂之间就一条公路通着,现在想想,公路一被炸掉,这些厂也就死掉了,炮弹运不出来,粮食运不进去,在里面生活的人生活就难过了,但是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分的散一点,可能好一点。所以1969年冬天珍宝岛一仗发生以后,我们这里很快的,筹建任务就下来了,南京军区派了一个叫韩克辛的师长过来,第一任后方基地最高指挥官,军区派过来的,他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接下来各个地方筹办,上级拨钱,跟地方上、省里打交道,定在安徽这个地方。地方上要出土地,要出人力,当时民工都是地方上出的。后面这套班子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到安徽的时候,韩克辛已经调走了,他们的调动很频繁。
凡是去后方医院的几乎是没有不回来的。因为凡是上海去的人,他为什么不回来呢?除非他和当地的结婚了,即使结婚他也有条件回来,因为他是从上海去的,他可以把家属带过来。只有当地招了一些人,当时因为圈地了,在那里造房子造医院,那么有几个进来了做后勤工作的,门房啊,洗衣房啊这些人。这些都是当地人,家就在蛤蟆坑周边。
医院撤回来以后,人都走了,但医院的房子和一切设备等全部留在当地,由当地接管。交给地方上后,那里变成了疗养院,据说后来地方上疏于管理,已经乱七八糟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设备都留给地方上了,但是医护人员都走掉了,技术人员走掉了。
医院的员工去向基本上分为这几块,一个是回瑞金医院,像张天锡、唐振铎这些专家都回去了,有的退休了,有的属于终身的一直聘着。第二部分都回到宝钢去了,二医大在宝山专门建了一个宝钢医院,相当一部分医生就是我们那个医院的人。还有一部分在公利医院,有段时间叫洋泾医院,现在回到原来的名称。公立医院是在浦东洋泾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区级医院,当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的员工,当然现在变了好多了。还有一部分在潍坊,潍坊医院是一个地段医院,潍坊街道医院。还有一部分,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在现在的浦东东方医院。我们当时的政策是这样的:你自己回上海找单位,只要那里要你就让你去。有的跑到了纺三医院,有的跑到了第九人民医院,也有的跑到仁济医院,有的跑到新华医院。不管怎么样只要找到一个医院要你,你留下来就可以了,这样就把关系转到上海来了,当时整个后方医院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医院周边的三线厂,基本上都跑在上海周边地区,跑到月浦啊,吴泾化工厂啊,宝钢那边。我现在已经很难再联系他们,有一个朋友呢我是和他比较熟的,他到美国去了,经常是回来的,现在已经过去了,没法联系。还有一个就在我们上大,在嘉定校区的,现在退休了,我知道他退休后住到苏州去了。这个人很重要,你们最好能够去采访一下。具体的地址我现在很难了解,以后有机会我可以通知你。这个人叫钟行书,他一直在后方基地管理局工会工作。因为我是在具体的单位,他是在后方基地局,在局里面他知道的情况可能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们现在可能采访不到了,就是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我们后方有四个医院,都由后方卫生工作组领导。他曾是后卫组政工科的,我也是政工科的,但我是我们医院的政工科,他是我上级单位的政工科,可以说他是我的一个顶头上司。他经常把市里面开会的一些卫生工作精神,传达给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一次。他是专门跑四个医院,还有宁国的古田医院,贵池的长江医院等。
后方走出来的很多已经变成弱势群体了,像这样的人物很少。因为从小三线出来以后到其他单位没有位置,我们医院里的很多领导跑出来以后,回到上海都是当副职的,人家原来就有位子的。等于是被人家重组以后,没有位子,只能做副手,但是你的行政级别又放在那里,也没办法。后来瑞金医院的很多人虽然都是专家,但是他们基本上不当科主任,有一个科主任叫罗邦国,他是上海瑞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现在也退了。 【over】
采访王志平
采访对象:王志平(原后方基地管理局工农厂安徽征地职工),任跃华(王志平的太太,安徽旌德县人民银行退休职工)
采访人:徐有威,吴静上海正规搬家电话,顾雅俊
整理者:顾雅俊、李婷
采访时间:2011年5月4日
采访地点:王志平家
徐有威:请问您是安徽哪里人?小三线是如何征地的?
王志平:安徽旌德。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吧。中国由于战争的考虑,还有苏联的讲法,将上海等沿海城市辟为一线,二线就像湖州这种城市,安徽这个角呢就小三线,和大西北的大三线当然还有一大段路程。安徽当时工业基础较差,没有能力接管军事工业,当时小三线过去以后,都是上海领导的,刚开始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等等弄弄以后就到了1965年、1966年,就开始动工了,上海建筑公司就开始造房子了。造房子为了不影响当地,而且为了让外面看不出,和当地徽州的民居差不多,很隐蔽。当时我们那个小三线的那个地方因为树木很多,当时有个老革命是上海劳动局局长的谈浩,他管三线。当时要征一部分地,我就是征地工,三亩地征一个人,这个指标都是上海劳动局去征的,后来征了140人,就意味着征了400多亩地。山上都不算的,山上的树是规定:三公分以上周长、一米以上高算五角钱一棵,就像现在造商品房一样。一亩地按照当地的平均收入,付三年的报酬。地是赔青苗费,比如一年5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三年下来1500斤,一百斤稻谷大概7块钱,按这个赔偿,因为米是卖9分一斤的。当时是很便宜的,工资也低,就十几块钱。当时农民,在旌德地区本来就是山区,地少,如果地都征光了,没有工作农民要饿死了。
当时2万多人去了我们旌德的三线厂,旌德无线电厂、有上无一厂、上无二厂、上无三厂、上无六厂、上无九厂、上无廿厂、上海光学仪器厂、上海探伤机械厂和上海档案馆等。到现在还是上海管的,现在好像还是属于上海管的,没有移交给安徽。当时最多的是上无二厂,那里叫井冈山厂。我们厂为了保密,当地叫工农厂,有满江红等,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叫法,毛主席的话。这些厂名都是为了对付当地的老百姓,实际上我们当时都有编号的,我们的编号是8370,在屯溪,是南京军区有个812指挥部,后来叫后方基地管理局,有几个工区,我们仪表公司是四工区。
徐有威:你在这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读过书吗?
王志平:农民,读了小学,1972年进去工作时20岁不到。兄弟姐妹6个,家里当时都想去,但只有我去了,上面派下来的指标,队里无记名投票推上去的。家里最起码是贫农,家里有一个党员或者本人是党员。一个队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都努力争取,这是好事情,到厂里就是拿工资的,吃商品粮的,而且农转非了。
徐有威:在你们村里征了多少土地?
王志平:我们村一共就去了三个人。土地也征掉蛮多的。不成比例的。像有的队里一亩地也没征也征了人过去,大家村里互相平衡。
任跃华:一个公社,大队,生产队,人民公社里统筹名额。
王志平:我们总共一个县140个,我们公社里分了70个,我们大队里分了30几个。地方比较多,名额多点,有些地方一个都没有的,附近的优先考虑。挑中了也没什么很开心,反正就这样。进去工资拿的低,还没一起去的当地的两个小姑娘工资拿的多。因为进去有两个工种,一个是普通工种,一个是技术工种,技术工种要学手艺技术的,我们男同志学手艺要两三年,第一年18块多。小姑娘是普通工种,就是后勤工作,食堂工作工作。她们进去有30几块,加上津贴有40几块。我父亲想不通,说我们男同志的真功夫比她们高,但工资拿的比她们低。但是3年之后我的工资升为44元。加上什么饭贴米贴总共50多块钱。
吴静:你去的时候,厂建好了没有?
王志平:差不多了。1969年开始出产品的。还有个别厂还没好,像原来的1971年上海那个光学仪器厂,原来是造在宁国的。宁国呢,刚刚开始在造厂,但是台湾那边探听到了这一动静,进行了广播,于是光学仪器厂马上就搬家了,搬到旌德去,叫险峰厂。
徐有威:你学了几年?学什么?
王志平:两年,上海师傅教的。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技术,真空镀膜。我是小学程度,但是学起来还好,不吃力,过的去。我和上海师傅从来不吵架,因为我老老实实干活,我多次评到厂长的先进工作者,做到了生产组长好了工段组长。车间主任没有做到,因为要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当地人去厂里了十几个,而全厂一共七百多人。我在十几个安徽人工资最高。因为技术最好,工资高点。
我们做蒸发器等,当时其实我们国内的不是很过关的,德国那边的好,四吨虾仁换一辆德国的机器。我们自己的产品宽度才70微米,80微米多算宽了,他们的则是280微米。我们国内生产的纸浆也不过关,都是进口的。原来嘉兴的民丰造纸厂制造的纸浆只能造7微米以上的,7微米以下的我们是造不来的。但是我们用的是进口的4微米的。因电熔容量大体积小,所以要用纸薄。
徐有威:工作累吗?
王志平:还好。都是捣糨糊。像险峰厂,举例说国家规定是亏损500万,如果你亏损300万,那你就算盈利200万。不亏损的想办法让你亏损。因为那时候上海人都想回来。很多小三线老职工是上海户口,子女户口也都是在上海,子女都还在上海生活。1970年之后进去的户口就迁到安徽。户口在上海的粮油关系都到安徽去了,粮食供应是安徽供应的,上海就供应肉票等副食品。每个厂都有小卖部的,都是上海运过去都到。
徐有威:您当时住在厂里面?教育可以可以吗?工厂中的工资级别情况如何?
王志平:家到厂里有2公里。平时都是不回去的,住在厂里的宿舍。小学到中学都有的。我和当地人结婚,厂里给我房子,算是客气的了,因为分房是按照女的分的。分房有两个阶段,结婚的话分配给你一套小房子。结婚了之后再分了一套。大概五六十个平方。是烧柴的,我们当是住2层楼的,算是老房子了,几家人家待下来的。蛮好的。当时没什么想法。房钱好像是1块钱还是2块钱。我们是按照芜湖造船厂的标准,比方当地33元,我们39元,还有进山补贴费什么的10块钱。后来也有奖金了,每个月5-10块钱,按照指标定的。班组长没有特别的地方,这是不允许的。当时很公平的。职务高多拿点这是不可能的,多拿一分也有的搞了,也没这种想法的。每个月看考勤假的。
任跃华:当时单子上是水费、电费和房费,加起来就几块钱。职工宿舍自来水费不要。我们的银行是为小三线厂服务的,所以每个月水费是1毛钱,刚开始是5分钱。
徐有威:那边有火葬场吗?有墓地吗?
王志平:没有,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专门有个地方是专门葬上海人的。我们那个时候叫八宝山。现在墓地好像是要开发了。死在小三线的尸体是不允许进上海的,要当地埋掉的,当时是怕传染病。
徐有威:那个时候仁济医院也派过人过去的?在那边的名字叫什么?
王志平:位于胡乐的古田医院。我们的劳保医院就在那个地方,生病了厂医务室看不好就到那边去,每个周六都有救命车开过去的,旁边一辆救护车开过去到那边去看病。我有一次去看病回来,病假工资扣了1块钱,配药配掉6毛钱,没办法的。来回车子一块钱。
徐有威: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王志平:我是1972年进厂,1986年离开。1986年时国家形势调整了,我刚刚说过,不亏也要让厂里亏,人心都散了,大家都想回上海,1976年去了一部分去培训了,是1972年的一批人,1969年一片红上山下乡没有了,1972年呢一部分人家里根据情况以后呢,分到外地工矿。由于年纪小,没有立刻到外地上班。在上海代训3年4年以后呢到1976年,毛、周去世后才去。当时有个原因,贵池那边的钢厂,我们无线电厂女同志多,但是钢厂那边刚厂男同志多,代训的女职工都分到那边去了。到我们的厂的来了160多个,只有20多个小姑娘,摆不平了,找女朋友有问题了。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刊登广告,为了找对象。全国各地的女青年都可以调到我们厂里去,这样一来,人心所向,没有朋友的想找朋友回上海,家属子女没有安排工作的想回上海,老了退休想回上海,这个情况,每次市里开会都要向市里汇报。市里正好改革开放,当时因为文革时期办的,改革开放了也不合时宜了。有些东西运来运气都是钱,比如说材料要从上海搬过去,要多少钱啊,什么都要上海运过去,成本太高了。所以就结束了,回上海。上海市和安徽省谈了下来以后,你这个厂留下来我要,但是人员我一律不收了。后就是设备、厂房一样。上海也不是无偿把设备、厂房给安徽,上海向中央提出个要求,说我这么给安徽多财产,上海的税利应该减掉点。安徽等于花钱买了这个旧设备。安徽的职工上海一律不收。但是年轻的时候进了三线厂,不能到了大老头了你上海不收,上海要给一批补偿金的。每个人都给了9000元安置费,这样我就留下来的。
徐有威:当时大家都想着回上海?
王志平:从一开始到最后从来就没有安心过。特别是1976年去的一批小青年,刚刚去嘛,他们过年不许他们回来。就在寝室喝酒闹事,想回家,哭,没办法。当时上海北站专门有一辆车专门开到我们厂,但是要凭介绍信才能买票,走不了,来不了。当时又出了几次交通事故。因为上海人开车子么对山区总归不太熟悉。宁国和旌德交界的那边有个弯很陡的。
宁国那边有几个厂也很好的,像现在海螺厂(以前是胜利水泥厂),也是三线厂。还有就是胶合板厂,联合机械厂。手榴弹厂我们去看过,他们窗子很低,一个人一个位子,蹲个位。屁股底下有口井,井口很小,很深。下面是沙,手榴弹不好就往下一甩。窗一低,很快就能跳出去逃出去,下面就爆炸了,有个盖子,没有问题的,上面很小,下面很大的,又很深。还有造那个打坦克火箭筒,40弹,40筒。另外还有海峰印刷厂,现在还在,高考的考卷就是在那里印的。老师出了考卷就到黄山去玩了。严格保密,解放军看着的。

徐有威:这个不会亏本,很多厂都是供销不对路才垮台。
王志平:对。安徽厂的延安厂后面也是供销不对路,黑白电视机你说卖给谁啊?彩电都没人要了,不要说黑白的了。
吴静:工农厂当时生产什么呢?亏本吗?
王志平:生产电容,包括薄膜电容、云母电容、和睦电路等。上无六厂生产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工农厂是上无六厂包建的。从我进去到最后出了的时候都是做这些,没有改过。当时计划经济,每个月25日12点之前产品必须进仓,完成任务。我们厂里还可以,不亏。聚会的时候二十几年没有碰头了,只顾讲话,吃饭都来不及,出来的时候还算年轻,现在都是小老头了。老的也有,师傅一级的。回上海后,就像一盘沙子往海里一撒,都找不到人了。他们在那里出过汗水、挥洒青春,有的收获爱情,年纪轻的么百分之百,年纪大点的么就少点,都在里面谈朋友、生孩子的。我们那个地方叫德山里,有5个厂,无线电厂里女的多,平衡平衡,也有找当地人,农业户口也要的,厂里算他们是大集体工人。后来差不多都找到对象了。
徐有威:你当时没找上海小姑娘?
王志平:没有缘分吧。当时有人找了上海小姑娘,后来蛮好的,小三线调整后一起来到了上海,有了上海户口。
徐有威:当地安徽人对上海人有什么看法?
王志平:小三线对安徽人肯定有影响,比方思想观念,服装、饮食等都有影响,见世面了。比如安徽人以前烧红烧肉不放糖,吃糖吃不习惯,后来基本也都放糖了。其实安徽人其实有点恨上海人,他们工资高,吃的好,穿的好。有句当地安徽人的话我不好意思说,他们说:上海人,吃得好,穿得好,死得快。彼此大冲突没有的,周日他们下来买买农副产品,走走人家也蛮好。上海人几乎每家都有当地的安徽朋友,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到上海工作呢?
徐有威:你们进厂后习惯上海的生活了吗?
王志平:都习惯了。上海人到安徽去也相当的习惯。安徽大米,上海吃大米要配给的,吃的都是籼米,安徽的大米还没有人吃。安徽人吃黄鳝,但是甲鱼吃的少,四角钱一斤。后来安徽人都吃了,但是青蛙还是不吃。
徐有威:小三线对当地的基础建设有贡献吧?
王志平:公路倒也没什么,当地有国防工办办公室,马路都是自己造的。原来发电厂没有的,当时不通电的,点煤油灯。后来还造了自来水厂,原来也没有的。
吴静:当地人说小三线去了之后哄抬物价?
王志平:那倒没有,计划经济。但是当地东西是好卖了。礼拜天早上老母鸡、芝麻花生瓜子就摆出来了。当地人现钞多了。带鱼都是上海运过去的,那边没有的。
任跃华:当地的带鱼有是有,但是都是腌过的,很小的。
王志平:当时小三线也照顾当地人。比如厂里放电影,一开始电影是在露天放,后来进入食堂放映了。我们厂里的职工去看门票是一毛钱,当地人去看是5分钱。食堂当做电影院,自己厂里放映机有的,但是片子都是上海运提供。基本上一个礼拜一次,两次少,每周都有看的。看电影么上海放什么,那边就放什么。像日本电影《望乡》就在我们厂里放映,当时是属于内部电影,按理说不能放的,旌德当地就不能放,但是我们小三线工厂就能放。因为上海放什么,我们小三线工厂就放什么电影。因为上海的广电公司进口有规定的,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上海的文艺界也经常来演出,比如杨华生等,都是免费的。在食堂里表演,我去看过,挺有意思。食堂的椅子就是那种前面放碗的。有发票子有号码,如果有认识朋友关系好点的,就可以拿到前面的好位子。有时候会和当地安徽人因为看电影打架安徽人要进来,厂里人不让他们进来。关系这样弄僵也不行,就给他们便宜点,他们说没有钱,1毛钱的票子就买5分钱。洗澡也要问当地人收钱的,洗澡也有吵过。
任跃华:每个厂都是不同的。工农厂当地人洗澡要收钱,卫东厂不收的。卫东厂是分一个礼拜有一天给本地人去看洗,不收钱的。他们刚去的时候,当地农村没有电,没有水,洗澡的时候就是一个木盆。
王志平:刚开始上海人也很可怜的。当时冬天下雪,上海的菜运不过去了,没有菜了,他们就和我们生产队里商量。生产队拿点咸菜,黄豆等来支援小三线的员工。总得来说,上海人和当地人、当地政府关系还过得去,当地人好像和上海人不搭界,上海人管上海,当地人管当地人,经济上没有什么搭界。
任跃华: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什么都要分配的。
徐有威:有没有会拿点钢材换点好东西吃吃?
王志平:也有,但是很少。拿点设备去山东换苹果吃的也有的。就是比较少。
徐有威:当地发生车祸时,如何处理?厂里上海人之间的关系好吗?和领导的关系呢?
王志平:有,但是很少,轧死一个人不得了了,一条人命赔个几千块。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大的矛盾没有。因为当时厂长,当时就厂革委会主任,他讲话算数。但是工人如果不买账,也会吵。很少有打起来的。加工资等不开心的事情总归有的,打起来的很少的。
吴静:小三线退出后,当地人情绪上有没有什么波动?会不会觉得失望?当地的物价有变化嘛?
王志平:没什么波动。他们觉得你们走了反而好,物价还能跌呢。但是当地的物价没有跌。后来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就更加不会跌了。像现在我们那个旌德县只有十几万人,到上海打工的就有一万多人,因为当地老乡都有上海朋友,每家每户都有,也是因为小三线的缘故。所以他们到上海来打工之后,对当地的资源开发利用就减少,树木都长好了,不用砍伐了,工业污染也少了。他们赚了钱寄回家,比如一人带1000块回来,1万人就有不得了的钱了。一年要多少产值?一两亿的产值能耗要多少?
吴静:你当时会到上海来玩吗?对上海印象如何、
王志平:会的。会派我来出差。有时候过来玩。我骑着自行车出来,路上也没什么人,没什么车。
吴静:工农厂整个退出是什么时候?你有什么反应?
王志平:1986年撤回。总归有点的,毕竟是去上海,不是去什么偏僻的地方,不是去西藏。我是差一点随着工厂去了上海。我因为这个工种需要我,我是班组长。厂里是要我的,本来想把我借到上海的,但是时间长了也讨厌的,会觉得对不起我,要么不要你,叫你来工作,不行的。走的时候厂长招待我们吃顿饭,他长最后和我握手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对不起你,这是国家政策,不是我不要你。我说我也不怪你,国家政策没办法。你们不是不要我。
我们征地工100多人,其中有些人不要去上海,各有各的道理吧,他们要种地、不想分居两地等。其中想一起撤去上海的有几十人,大家去过我们的上级的公司,跟公司领导说过,但是这没用的。公司里说上面有规定,他们是按照规定办。我们说现在不都是双向选择了么,工厂可以选工人,工人可以选工厂。我们觉得你们工厂蛮好,那么你们也应该选我。公司的人说这个和我没关系的。我们骑自行车去公司里的,但是公司用汽车送我们回来。
我们厂搬过来搬在上海的南大路,在南翔不到一点的地方。我当时还押车送设备上海,是小三线的683车队的车。我们是半夜送出来。厂里比较信任我。
徐有威:因为你是安徽人,在当地的检查会比较好通过一点?
王志平:没有,都要查的。我们搬出来一个3车间,其他都留在那里。
徐有威:当时不是说都要留在那里的么?不能搬出来的?
王志平:协议签之前就能搬了。能搬的都搬出来,不然不能搬了。有一个时间结点,过了这个时间点之后仪器就不能搬出来了。井冈山厂回到了上无四厂,立新厂也回到了上无四厂,上无四厂没有支内,但是收了不少支内职工。
吴静:当时不是说小三线的工厂不能进市区么?
王志平:没有这个规定,只要原厂接收。我们刚开始在南大路那边,我们工农厂一个车间搬出来,六七百人在一起怎么行?活都没有,计划经济结束了,贷款都贷不到了,工资哪里发? what to do?继续找啊,后来找了桂林路这里的上海录音器材厂,这个厂本来就两千多人,退休工人三千多,进来六七百人,混了几年又不行了,又拆倒闵行去了,所以后面叫闵行塑光厂,索尼和上海广电合资,搞了一个小的塑光,造摄像机的,效益不怎么好。
顾雅俊:现在留在安徽的上海人还有吗?
王志平:要么回来,要么退休,旌德的也有,要么退休,要么去世了。
徐有威:当时厂里有什么带回来的照片文件吗?
王志平:没有了。当时保密厂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
吴静:那里的银行为小三线服务做什么工作?
任跃华:什么都做,发工资,存款,工资到那里拿,叫303办事处,是人民银行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屯溪下设的,里面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我是80年去的,但是三线厂成立了,这个银行就成立了。他们的钱等于是存在银行里,比如说每个月哪一天发工资,财务科的人就到他们那里去取了。贷款是不可以的。小三线撤走之后,银行也撤了并到县城里面了。
徐有威:小三线的工是上海移送给安徽的吗?
王志平:不,是安徽出钱买下来的,安徽多交钱给国家了。但是它买下来的是净值,这个设备用了多少年了,净值多少。这个表我是看到过的,各个厂都有的。有张清单的。当时的净值买下来的,折旧都折掉了,房子也是折旧的。总价多少我不太清楚。
徐有威:你后来到上海来,他们有没有帮你的忙?关系你自己建着的?
王志平:也没帮到什么忙,我到上海毕竟有些基础,上海人的爱好什么的我都大概知道,可以投其所好了。原来的同事等他们出来都做工人了,我和他们推销也没多大关系,我本来是工农厂,后来到延安厂了,本来做电容的,后来推销电焊气,所以是没有关系的,电视元件多着呢。不过因为之前来过上海,上海也有些朋友,胆子也大了,到上无四厂、上无十八厂等推销,还方便一些。
任跃华:里面几个厂当地接收下来后,也没有管理好,都散掉了,到上海后也大多都散掉了,特别是险峰厂。
徐有威:那你当时是留来的?
王志平:对,我是留下来的。留下来以后呢,我们工农厂是安徽集体单位接收的,我之前工农厂是国营单位,我就转到上无十二厂的延安厂。由于我在上海有基础,所以厂里让我1990年以后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没有回去过。我没有户口,退休也是在安徽的,2007年病退,工资不发,给提成的。安徽给我退休工资,一千多块。医疗报销都是也是安徽。现在医改,一年报销不会超过2万元。在上海可以住院,但是只能生大病了在上海看的医疗费才能报销。我们是八几年结婚的,太太退休后才到上海。开始在上海租房,在2004年5月在上海买了房子。混到现在身体坏了,把房子卖了,现在在上海租房,准备回去老家了。
徐有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后有机会一定去旌德看你,采访一些安徽的老同志。
【超过】
上海蚂蚁搬场运输有限公司04年成立,牌子老,服务好,收费合理,是您搬家不错的选择!